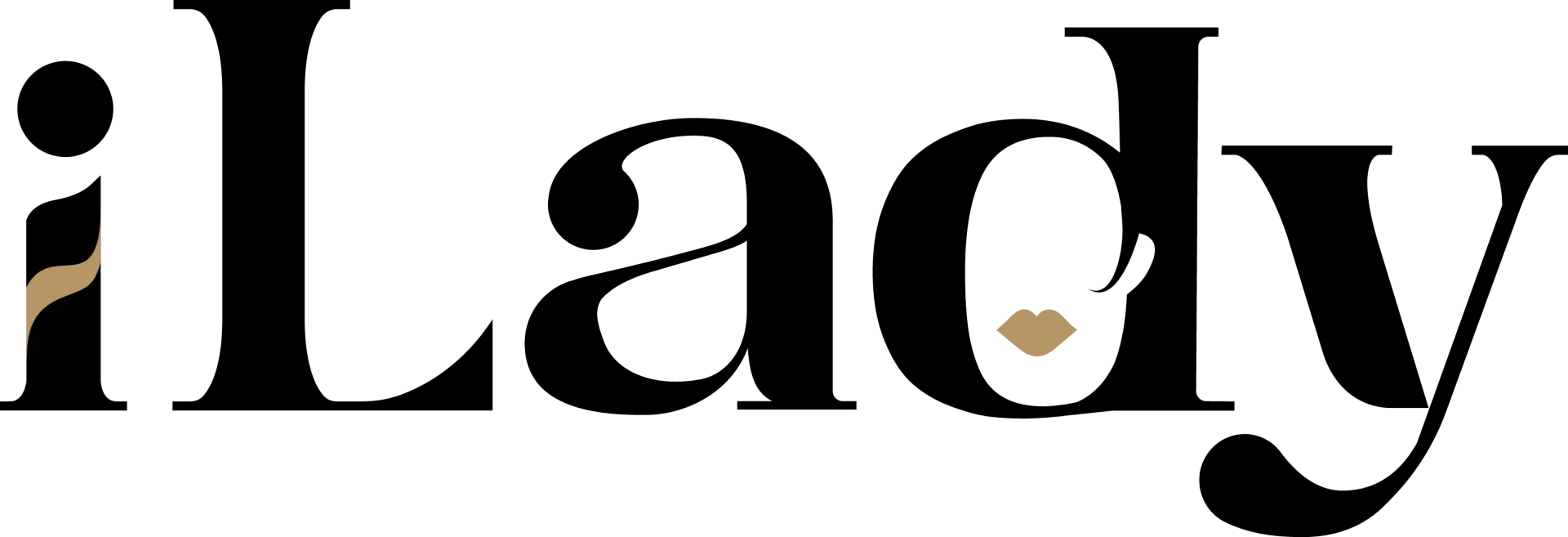在許多人眼中,髮型是風格的一環;但在電影髮型師 Laurance 勞綸的世界裡,一個髮型就是一個角色、一段敘事的起點,甚至是產業生態的一面鏡子。
從髮廊剪髮到影視現場指導,勞綸合作過梁朝偉、金城武、陳奕迅等影視音樂巨星,再到今天成立團隊、推動教育,他走過近二十年的轉折與磨練,從不斷問自己「我還能做什麼?」到如今願意反過來問:「我能給後輩什麼?」透過這次專訪,勞綸對專業的堅持,讓人忍不住也心生澎湃。

專訪電影髮型師勞綸。(圖/勞綸 提供)
拿剪刀,從不是一場衝動
如果人生能有幾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勞綸的轉彎發生在高中。那時他念的是資料處理科,一門通往工程師的穩定路線。但他很快意識到,自己其實只愛「玩電腦」,對變成職業毫無憧憬。轉念之間,他看見了一位學長——一名剪頭髮的設計師,身上有著說不出的自信與自由,他笑說:「我發現自己想成為他的樣子。」
21 歲那年,勞綸正式入行,第一位師傅是許多巨星指定的知名髮型師,「當時我的學長剛好在那裡工作,我就跟進去了。」他從學徒起步,累積扎實技術和設計功力後,到另一家髮廊、接觸到唱片圈,合作過五月天、周湯豪、MP魔幻力量等知名歌手的演出造型製作,協助唱片造型、跟拍攝影棚、處理藝人造型,他累積經驗、理解產業脈絡。
後來,乘著當年第一批髮廊系統進入劇組的時代轉變,他慢慢踏進影視圈,靠著電影《艋舺》、《明天記得愛上我》中獨立出師,成為真正的電影髮型師傅,同時也是許多影視藝人指定設計師。
從 2005 年踏進美髮圈,到今天,勞綸已經剪了整整二十年。

專訪電影髮型師勞綸。(圖/勞綸 提供)
走進影視劇組:每一根髮絲的精準執行
髮型指導的工作,從劇本一到手就開始。除了分析角色造型、提出設計提案,還得計算人力、分配預算、組建團隊、與導演演員開會溝通,歷經多次「一定二定」,最終定案後才能開拍。
髮型在電影裡,是潤物細無聲的敘事。髮絲的長短、捲度、濕潤程度,甚至沾上的血、染上的沙,通通得與劇情、情緒、拍攝順序、演員狀態配合無誤。「拍片不是隨心所欲的創作,是精準嚴謹的執行。」
他坦言,過去拍片時,緊繃到幾乎失去生活。拍一部電影,進組至少一個月起跳,影集可能要拍半年以上。造型組往往比開拍時間提早三小時進場,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起跳,連假髮分區貼合的方向都不能錯。
除了拍攝前置的設定、人力規劃,現場也得跟著演員、調整髮型,勞綸說,「我們拍電影要的,就是頭髮長長了還能變回原樣。不能多剪、不能少修,一絲不苟。」

髮型師勞綸曾負責過多部影視作品髮型。(圖/IMDb,MyVideo)
最難忘的現場,是王家衛
談起電影經歷,勞綸毫不猶豫說出《擺渡人》是他最難忘的作品。那是一場藝術與壓力的極限拉鋸。
「王家衛導演會讓全世界暫停,只為了等我弄好假髮。」勞綸提到,最初劇本設定一幕梁朝偉看到黑長捲髮的女子,但導演在現場看到造型完成後,臨時決定改成瑪麗蓮夢露式金捲髮,現場瞬間變陣,所有人都停下來看他換出新造型。
勞綸笑說,這場景、這氛圍和當時背負的壓力,至今仍讓他印象深刻。
此外,當時電影原訂拍兩個月,最後拍了十個月。期間助理換了三輪,除了要處理不同夥伴之間的磨合、導演和劇組的變動與要求。種種磨煉下,他深切體悟到:「我不能控制所有人,只能盯緊每一件事。因為工作這回事,就像王家衛導演說的:No Excuse.(沒有藉口。)」

專訪電影髮型師勞綸。(圖/勞綸 提供)
用專業換來尊重,是一生追求
「我認為髮型也是一項很高深的職業,當每個人初始條件、環境等各種影響參數都不同,髮型設計師要了解幾何結構、在基礎裡做空間設置,了解目的和起點後再展開過程,每一步都是在考驗我們設計路徑的能力。」
曾經,他也被貼上「大牌又貴」的標籤,但他說:「髮妝造,常常被笑是『劇組三毒』。但我從小就被教育,工作是要做好頭髮、照顧好演員。所以我不嬉鬧、不攀關係,我只希望用專業得到尊重。」
他近年逐漸減少影視案量,將重心轉回髮廊與教育,結束影集《不夠善良的我們》、電影《周處除三害》等作品之後,從工作第一線退到人才培訓。
勞綸坦言,他發現電影造型這一行的傳承岌岌可危,因此想從教育著手,提供訓練、創造平台,也協助有志進入影視的設計師取得作品與人脈。「我不是要大家拜我為師,而是要培養他們能靠自己站上現場。」

專訪電影髮型師勞綸。(圖/勞綸 提供)
當髮型助理出現斷層——轉身成為教育者
說到這裡,勞綸不禁提起台灣影視圈的某些困境——加班文化、低價競爭、專業不被尊重。「這幾年,我發現自己越來越難找到助理,找到理念一致的人不容易,技術人才也出現斷層。」
勞綸感嘆:「大家都知道外國環境好,但回到台灣環境,卻常常變成另一種對待。」他分享自己曾經遇過在同樣的台灣劇組裡,合作的香港團隊有超班費、零用金;但反觀台灣自己人,卻得降價競爭。「我覺得,這是產業無法進步的根本原因。」
如今他不再衝撞體制,也不再忍受被輕忽的待遇,但他想試著用品牌、用教育、用一群人,去緩慢但堅定地重建這份工作的尊嚴。「年輕時做美髮,是我耍帥、想表現。但現在,是我想讓別人發光。」
技術和觀念教育並進:想為影視圈投注新的力量
平時,勞綸除了在髮廊黑鵝摩沙進行預定服務,也籌組了自己的品牌團隊——BigSmile Wedding,主打高端造型與教育輸出,並計畫開拓婚禮紅毯市場,讓新娘新郎成為故事的主角。
「過去在髮廊,更像是幫自己工作,乘著髮廊資源提升自己的經驗、信任跟專業。現在以品牌組團,我希望能讓團隊裡的人信念一致,大家一起往同個方向前進。」
勞綸說,透過新的品牌體系,他希望做好技術和觀念教育,並對那些願意真正投入,且具備至少三年技術經驗的人才中,他也樂意給舞台、給資源,甚至給合作案,期待他們有機會為影視產業投注新血。

髮型師勞綸(左)想試著用品牌教育,重建影視髮型工作的尊嚴。(圖/勞綸 提供)
每一位設計師,都值得被看見
回望自己的成長,他說這行沒有天賦說,只有是否願意「做到底」。他鼓勵年輕人先從髮型技術紮根,再學會與人交流、進入影視場域。「別想一步登天,也別怕走回頭路。」
今天的勞綸,不只是一名髮型師,更是一位構築職涯新可能的導師與實踐者。他的路,從影視走向品牌、從技術走向教育,轉了好幾個彎,卻始終沒有偏離他心裡的信念。「市場是年輕人的,我們這一代要成就你們。但也希望你們記得,自己有被成就的責任,也有未來成就別人的義務。」
在這條長長的職業路上,勞綸像個剪刀行者,一邊走,一邊剪,一邊傳承。「教育才是解決這一切的根本,把人留住,讓台灣影視恢復競爭力。」他持續修整髮絲,也期望修補一個產業的未來。
延伸閱讀:
她。百業 34|電影造型師媛梓的一天:「服裝組的拍片日常,經常是狼狽的搶灘戰」
專訪|15年從街頭到國際舞台!台灣馬戲 FOCASA 團長林智偉的 100 次勇敢
專訪|書寫人性浮世繪,社會記者李隆揆的工作一天:「新聞不會等你。痛並快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