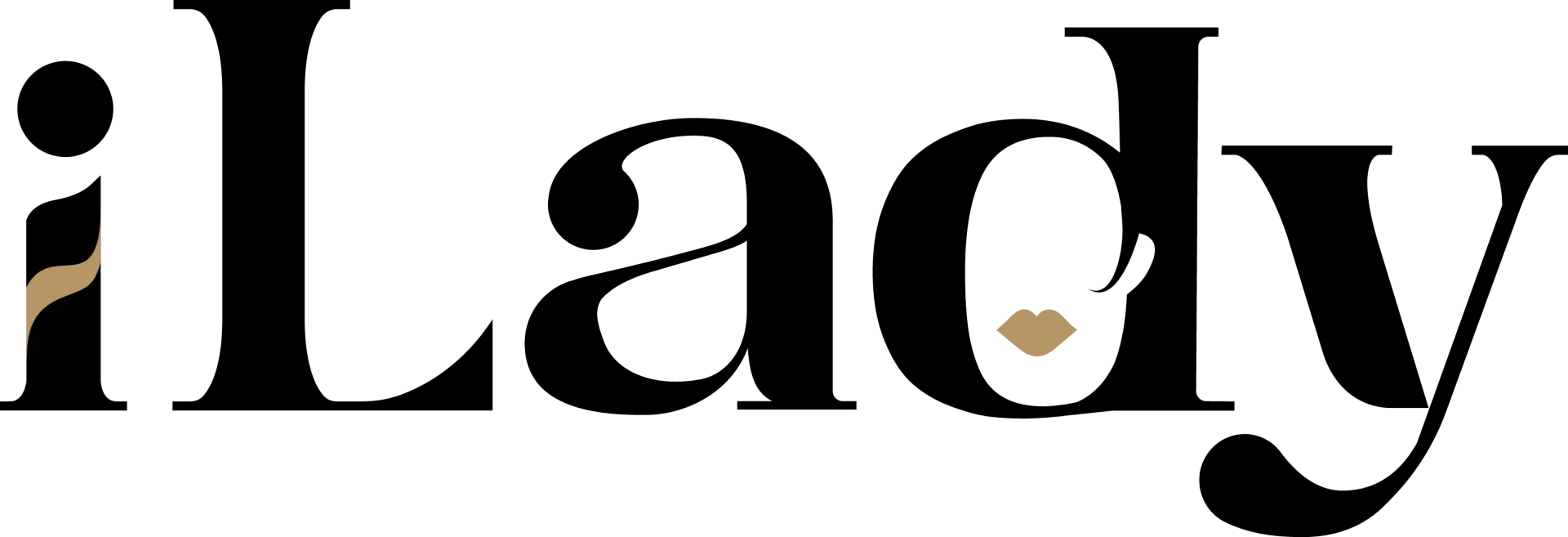現在人人都愛美,從臉到身材、穿搭通通都要保養好、裝扮得體,這其中也少不了「髮型」。有一說:「髮型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美醜」,雖然有些 Lady 天生臉蛋漂亮,光頭也是美人胚子,但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會有一個信任的髮型師在為自己打理設計每一次的新造型。
這次筆者邀請到這位髮型設計師 Amos 很特別,他曾在繁華的台北西門町,是知名髮廊的紅牌設計師、月入數十萬不說,想要預約到他的時間,比訂高級餐廳還難。
不過 8 年前 Amos 帶著三個徒弟出來創業打拼,地點同樣選擇在這個充滿他人生大起大落的「西門町」,不只培養更多美髮人才,更帶著團隊到處義剪、體驗人生,他想告訴後輩們:「你的技術不只值錢、還值得有愛。」

非專科出身的 Amos 從學徒做到設計師,只花了三年的時間。(圖/Amos 提供)
非專科出身 意外踏入美髮圈
Amos 並非出身於美髮專業,他大學就讀企業管理,在校時,一度對未來感到迷茫,不知道畢業後應該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大學期間,他曾經當過酒保,處女座性格的他,總是追求極致、把事情做到最好。他把酒保的工作做到連老闆都賞識,希望他畢業後留下,但日復一日的工作,讓他反而渴望尋找未來新的可能性。
Amos 的外型從小就比較中性化,在那個社會風氣不夠開放的年代,Amos 總是得忍受那些性別歧視、訕笑,在思考未來出路時,礙於不少工作有性別上的限制、甚至有些還得分男女制服,正當他苦惱不已時,他和自己和配合已久的美髮設計師聊到職業,交談中,設計師向他描述了這個行業的自由氛圍,並提到收入可以高達月入十幾萬。
這一番話讓 Amos 相當震撼,心想:「就是這個了!」他毅然決然踏入了美髮業、成為學徒。那時正值台灣美髮業的全盛時期,他在西門紅極一時的髮廊學習,員工就有4、50 名,但 Amos 很快發現,月收入十幾萬的設計師只是極少數,可能只有三個人可以達到、甚至有些設計師需要向助理借錢來度日。「我真的嚇壞了!怎麼會是這樣?」Amos說。

Amos 為了跟上美髮趨勢,直到現在都會不定時帶著團隊一起上課進修。(圖/Amos 提供)
不服輸的性格 接受挑戰與成長
當時一個月薪水才領八千,Amos 大喊:「我真的窮死了!」他會看著其他設計師或助理的食物,問他們:「你吃得完嗎?吃不完給我吃。」他覺得這樣不行,他一定要成為店內前排的設計師。
所以他也積極到中國上海、香港,還有英國沙宣學院進修,Amos 經歷了非常嚴格的培訓,看透了許多美髮圈裡的黑暗,這些經歷讓他明白,不是每位設計師都能輕鬆成功。他說:「升為設計師需要六年以上的磨練,是一場跨越十八層地獄的旅程,但是我花三年,我擠破頭成功了。」
沒想過創業 但他開了自己的美髮沙龍
當了十多年的紅牌設計師,Amos 曾帶著三個徒弟和一位投資人合作,由於理念不合,又不能放下徒弟,自己離開,所以他創立了自己的美髮沙龍—去兜 kidulthair,他說,從決定拆夥到去兜成形,我只花了不到半年的時間,我從沒想創業,但為了生存還有徒弟,我頭洗了就是要繼續。
西門町成為 Amos 創業的起點,對他來說,這裡充滿回憶,也充滿年輕與創意的活力,是孕育新潮流的絕佳土壤。他將這份對地區的熱愛融入品牌,讓去兜成為許多年輕人心中的時尚地標。
但想當美髮師,或許容易,想當優秀的美髮師,那真的不容易。Amos 認為,一名優秀的美髮師,必須具備換位思考的能力,懂得聆聽客人的需求。對他來說,美髮不僅僅是技術的展現,更是一種藝術與客人情感連結的過程。
去兜在這方面尤其突出,他帶領團隊不僅追求技術精湛,還注重社群媒體的運用,讓更多人了解去兜的理念。去兜的成功秘訣之一,是 Amos 鼓勵員工參與決策,讓每位成員都有自主權。
在這個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有一段時間,店內的每位員工每天必須拍攝兩支影片,從觀眾的反饋中不斷修正內容,確保品牌始終與市場需求同步。

Amos 帶著團隊義剪,要他們擁有技術的同時,也要懂得創造愛。(圖/Amos 提供)
美髮人不能只有技術 為愛與陪伴而努力
除了商業成就,Amos 與團隊還長期致力於義剪活動,服務對象包括老人院、孤兒院及原住民社區。他回憶起一次在養老院的經歷,特別提到一位可愛的阿嬤。這位阿嬤性格活潑、喜歡打扮,常常看到他們來服務,就會很親切的說:「恁來了喔!」、「我今仔日想欲按呢剪」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某一年 Amos 發現阿嬤臉上的笑容不見了,詢問護理人員才知道,她的老伴因病離開了老人院,阿嬤也因此患上憂鬱症。即使如此團隊還是盡心盡力的為她剪髮,還陪她聊了許久,雖然後期阿嬤因為老伴走了、她也跟著離開⋯但至少大家陪伴阿嬤這一段路,她是開心的、團隊的心也是暖的。
Amos 深刻感受到陪伴的力量,「技術曾經帶給我很多錢,但到最後,我發現,錢不是最重要的東西,因為那時候的我,只剩下錢,那麼技術還可以給我什麼?」 他說。
打開視野 才是改變世界的開始
Amos 堅信,美髮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帶給人愛及改變世界的一種方式。他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把過去那些讓他感到不安的環境,轉變為美好的樣子。
過去大家對於美髮人的刻板印象,Amos 努力在去扭轉翻新,他認為每個人無論是什麼背景,只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你的技術、你的能力才有意義。

員工旅遊也是 Amos 希望能夠帶著團隊,開創視野的一個方式。(圖/Amos 提供)
延伸閱讀:
「媽咪,我來親你一下」小男童面對失去至親仍然樂觀,身為大人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